| 1890��7��3���Ї��v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㡳�����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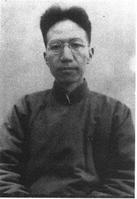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”����“kè”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“què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Ԯ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ͨԒ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x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[1]��1890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Lɳ����1969��10��7�����ڏV�ݣ��Ї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ؓ(f��)ʢ���Ěv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ČW(xu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ԌW(xu��)�ң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ꐌ���֧��׃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ᣩ֮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J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Ѳ���ƾ��µČOŮ���Ҳ��һλ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־ͬ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37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ٕr(sh��)���Ͼ����Ӿ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ͥ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ܱ��b�ĕ��彛(j��ng)���V����x�vʷ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伮���
��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ʮ���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ֺ�㡖|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㼲�z�W(xu��)�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꿼ȡ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ִ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ʿ�K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У���x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궬�ֵ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ٶɳ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S�@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���ĺͰ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S·��ʩ���ڹ��x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ڌ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Ё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ʿ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ɹ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ڊ^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Ҿ߂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°˷N�Z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Ͱ������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ʷ�W(xu��)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㡻؇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ƞ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о�Ժ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F(xi��n)���Ŀ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Ƹ�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Ԫ�ε��˞錧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˷Q���A�Ĵ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о�Ժ���΅�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“ȫ�Ї���W(xu��)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ĵ����˽�B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ҡ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У���e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26��6�£���ֻ��36�q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һͬ��(y��ng)Ƹ���о�Ժ�Č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“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^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2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(d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˼��”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r(ji��)ֵ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ڇ��W(xu��)Ժָ��(d��o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n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̵伮��߅��ʷ�M(j��n)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W(xu��)�_�O(sh��)�Z�ĺ͚vʷ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n�̡����v�n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N�Z�ԣ����C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eʷ���ġ��B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衷�����ſ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̎������֟o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l(f��)���Ǿ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ˇ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t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W(xu��)�߱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A���W(xu��)Ժͣ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W(xu��)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ϵ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о�Ժ���¡��vʷ�Z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һ�M�M�L����ʌm����Ժ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Ǭ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C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Ŀ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“�vʷ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ݻ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vʷ���̽��ʷ�ϣ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ϵĿ��C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һЩ�Y�ϸF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ӆ�_�С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⌦(du��)ʷ��(sh��)�ľC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п��C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Qһϵ�І��}����Úvʷ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ܿ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ͳ��^Ǭ¡������Αc�r(sh��)�ڵČW(xu��)�ߣ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҇��Ěvʷ����(j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㡌�(du��)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퍌W(xu��)���ɹ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}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о�Ժ�vʷ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W(xu��)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ȿ����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ƪ���з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繫�J(r��n)�IJ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Ҋ�R(sh��)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Ց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܊ֱ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㡵ĸ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^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L�š��Ά��ꮅ������SУ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У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շ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܊��ռ���Ϻ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һ�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ȡ���V�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ΏV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ƾ��ྩ��W(xu��)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շe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㡸е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Y��ʯ�I(xi��n)�Ŷ��ğo�Ļ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ո��x����“�Ŷ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c����ؚ”������ʾ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ڷ�æ�Ľ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ƶȜYԴՓ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ʷՓ�塷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µ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ʷ�_�����µ�;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Α�(y��ng)Ƹȥţ���W(xu��)�ν̣���혱㵽�����ί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Ӣ�t(y��)�\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oЧ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Ŀʧ���ѳɶ��ֵ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㡑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ȥƸ�s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^�ˇ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о�Ժ�vʷ�Z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˹��Ҫ��ȥ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Ƹ���ν��ڏV�ݎX�ϴ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Ժϵ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ϴ�W(xu��)�ϲ�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ܵ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͟o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x���Ї��ƌW(xu��)Ժ���(hu��)�ƌW(xu��)��ί�T���Ї���ʷ�^���^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���(w��)ί�T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Ї��ƌW(xu��)ԺԺ�L��ĭ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οƌW(xu��)Ժ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(hu��)�ƌW(xu��)�vʷ�о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Lӛ�d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o�xδ�ͣ��]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ˮ�h־�塷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㡢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ܓ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ˣ����Ⱥ�ȥ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ۼ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o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ʿ݆������ڏV�|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w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ľЦ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ֵ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ƶȜYԴՓ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ʷ��Փ�塷����Ԫ��Ԋ�{�C�塷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ࡢ��(j��ng)֮�I֮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ɴ˸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��”���
����ʮ���(d��ng)�y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౻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꣱���£����ڏV�ݺ����x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ڽ̌W(xu��)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(y��n)�C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о��Ќ����˸�ˮƽ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_���˚vʷ��ҕҰ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҇�ʷ�W(xu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ؕ�I(xi��n)��һֱ�ܵ��˂��ij羴�������㡲��H�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wԊ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Y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ۺ�������x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eϲ��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ՓԊ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w”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Ԋ�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Y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ֵġ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꾎��Ƀ�(c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20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(d��ng)��“����֮˼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”��1953���ћQ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ƌW(xu��)Ժ�vʷ�о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1953��12��1�յġ���(du��)�ƌW(xu��)Ժ�Ĵ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ăɂ�(g��)�l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“���S�й�ʷ�о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R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ڶ��l��“Ո(q��ng)ë�����oһ���S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߮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߮�(d��ng)��Ҳ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ͬ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֮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”�첻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80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㡵�“�IJ��v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ĵȶ�N�|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֡��w�����Ⱥ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W(xu��)�о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ϴ�W(xu��)�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О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漰�vʷ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̵ȶ���(g��)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µ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µ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V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V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Ⱦ��Ъ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“ǰ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^ȥ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v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ֻ�vδ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㡵��n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塢�T���m����嵡�����ĵ��h�W(xu��)��䓺�̩�ȶ��L(f��ng)��o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v�W(xu��)߀ע����Ȼ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µİ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ָֻ��(d��o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ğo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ՌW(xu��)У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в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f:����ʽ�ĹP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ƪlun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:��Փ��Ҫ���µ��Y�ϻ����µ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Ϻ�Ҋ�ⶼ�]��ʲô��ȡ�����t��Փ��Ҳ�]��ʲô��̎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ښvʷ�о����ĵ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:“����Ҫ�ľ���Ҫ����(j��)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C��ʷ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(sh��)ʷ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(du��)ԓʷ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cʷ�R(sh��)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”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ؑ���:“ꐎ����v�vʷ�о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:��ǰ�ˌ�(du��)�vʷ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?n��i)��Ҫ�C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ֻҪ�܉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һ���N�e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’�ˣ����Ҫ�C������‘�o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ί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ף�ǧ�fҪС�ď��¡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�N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Ҋ��‘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Y���Ǻ��y�Rȫ�ģ��F(xi��n)�е��ļ��mȫ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е���δ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?q��)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Y���Կ��C�����‘�o’�أ�”���㡌�(d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о��ć�(y��n)֔(j��n)�B(t��i)���ɴ˿�Ҋһ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ָ�˹�ꌦ(du��)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@�ӵ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:“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̄�(w��)ӡ���^����ġ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h�Z�~�䡷��2002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”��(y��ng)�x��“��”(ƴ����kè)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Y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”�ڿͼ�Ԓ����“quó”�ģ�����ͨԒ���r(sh��)�Q“���Z”���П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㱻��(d��ng)Ȼ�طQ��“yínquè”�ˡ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(x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“����”��(y��ng)�x��chén yínquè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ʹ�Ýh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@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@Ȼ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ͨԒ�r(sh��)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㡵�“�”�x��“��”(kè)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�����1940��5����Ӣ��ţ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Ӣ���H�P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“tschen yin koh”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Ŀ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ϱ���ʷ�v��䛡������H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Pӛ�����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ȜYԴ��Փ�塷
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ʷ��Փ�塷
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Ԋ�{�C�塷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㡌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Ļ��S�P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
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ӛ
��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㡡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ƌW(xu��)�īI(xi��n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ƌW(xu��)�īI(xi��n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磬1997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I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㡵�����ʮ�꡷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7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Ҫ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Ц����ʮ�꡷
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ȣ���Մ���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ČW(xu��)
������Ӣ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|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Ĺ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ʹ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3��11��0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㡵ļ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0��
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f�x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|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㡺��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Ӣ�����磬2007�꣬isbn 9789867762832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֣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㡎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(xi��ng)��|�����X��Փ���㡣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�δ���_�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Ⱥ����2008���3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1923��8�¡��W(xu��)�⡷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��㡕��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
������ȫ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ȳɞ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ܱ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ÿ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ɝh֮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@�䲩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T���^��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N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Փ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㡞�ȫ�Ї���W(xu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’��r(sh��)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К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֮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�(ji��n)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֮ͬ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mϵ���Ѷ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˹�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1937��2��22�յ���ӛ�зQ��“���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
������ʯȪ�LՄ䛡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˼���е��Ј�(ji��n)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˅s�����m�Q��“�z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ڕr(sh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v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B(y��ng)�O�s�O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λՓ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g�ӂ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ֲ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Ҷ��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W�ޣ��cϣ�D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֮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ˇ��Ҳ����亦����tչ�D(zhu��n)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Ļ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´˲���֮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ֱ���о����Ļ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f“�Ļ���ԭ”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u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m֮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ˡ�
�����Ȳ��纣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X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Ԋ��Ҋ�䌦(du��)�Y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ʧ���c���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ǧ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ɑz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ɮԒ�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o�u�_(t��i)�Ǒ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F(tu��n)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Թ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Î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ė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Ԋ����ֿ�Ҋ���䌦(du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n)�h�IJ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՚�ʮ�ֵĉ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и�Ԋ�ƣ�̎���ڲ��IJ���֮�g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̼Ӱ��ۡ�
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¹�Ц�R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pĿʧ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ʮ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@�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ɫ�ʡ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Xլ�t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֘O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ͨ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֮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r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څ��֮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ʷ��Փ�塷
����Փ�ƴ�֮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ĩ�|���T��ؔ(c��i)��֮�^(q��)���Ɖ��c��·�\(y��n)ݔ֮�Д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ǣ�“��|�Ͻ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Ļ���(qu��n)�S��֮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첻�ò��A���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٣����A�@�ĸ`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u����ُúȡů���ĸ�r(sh��)�ļt�l(w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Ե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57��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֪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忬����֪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ָ���£��w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E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忬�ȷǷ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G֮�ҳ�����Ҫ횾þ��b�x���ɱM���Ԋ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֮ƪʲ�ښ��I����֮�ţ������QҊ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־�������°�֮۫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Ԯ�(d��ng)��֮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(y��ng)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媚(d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r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T֮��Ů���I����ɪ֮С�D���֞鮔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֮���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㡼�(x��)���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֮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ʼ�K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֮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Ÿ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����r(sh��)݅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֮�о�“�t�y”֮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Բ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Σ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£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֮�挍(sh��)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^�����e�L(f��ng)Ȥ֮�Є�(d��ng)Ҳ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ж�ƪ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־�I(y��)�c˼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һ�r(sh��)�H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Բ�֪���㡞�u���@��(d��ng)�к��Џ�(f��)�s�ĕr(sh��)��˼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ʷ���ˣ����ɲ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һ�F(xi��n)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ӳ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Ї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r(ji��)ֵ�ļ�(x��)���c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N�N������cǰ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v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£����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̣�ǰ���е��Ҳ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|�x�T�y�ƶ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���Փ�ܡ��R֮�����^�c(di��n)“����(qi��ng)”�c“���M���Ϛvʷ��(sh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܄׳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˼�桷��ӛ�Ю�(d��ng)���W(xu��)�ߌ�(du��)��ό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�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O�S��ֻ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˼�룬�ԃH����һ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㡂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X��ƽ�\������δ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ď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c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Ϟ��Ї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ʷ�ϘO������ɫ�ʵ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һϵ���Փ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H�˶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e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ˣ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ϲ�R���·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ˮ����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˼���е��Ј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^“����⽮�����ȸ߹ټ�ͥ���ӵ�”������@�Ǻܿɹ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˅s�����m�Q��“�z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ڕr(sh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ɞ�һ��(g��)“��į�N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v�O��W(xu��)�B(y��ng)�O������s�O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λՓ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Y��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83������Z�ƣ�
�����g�ӂ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Ҷ��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cϣ�D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ɞ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֮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ˇ��Ҳ����亦���tչ�D(zhu��n)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Ļ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´˲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ֱ���о����Ļ���ԭ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f“�Ļ���ԭ”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u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m֮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cꐶ�����һ��ѳ�Ї��Ļ�“���V���o(j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֮˼���c�˸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ܸQ���N(y��n)�W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Ȳ��纣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^�X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h�Ҍ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Դ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·DZ���(z��i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㡌�(du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ȫ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՚�ʮ�ֵĉ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и�Ԋ�ƣ�̎���ڲ��IJ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Ԋ�г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˴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磺“�����ν̼Ӱ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“ʣ�����¹�Ц�R”��“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Լ�“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N��”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˵Ŀ��ſɂ���“��ʷ”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Ĝ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܈�(ji��n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囶����ᣬ�Fʮ��q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Xլ�t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ؾ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”��“�üt���̜I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n��֮���^“�ڸ��Ԟ鼈�����rѪ�ԕ��~”��Ҳ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vʷ�^��ע�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(d��ng)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ؾ����(d��ng)Դ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ʷ��Փ�塷Փ�ƴ�֮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ĩ�|���T��ؔ(c��i)��֮�^(q��)���Ɖ��c��·�\(y��n)ݔ֮�Дࡣ��Y(ji��)Փ�ƣ�“��|�Ͻ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Ļ���(qu��n)�S��֮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첻�ò��A���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ͨ����“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֮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r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څ��֮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Ψ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ɌW(xu��)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˵ľ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ؕ����Ĵ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A�@�ĸ`�\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u����ُúȡů���ĸ�r(sh��)�ļt�l(w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“�o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o֮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��ւ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ʧ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[�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w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Փ�����ϷN�N������֮�(d��ng)��“��ϲ�R��”��“��ͬ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ڣ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Ԋ֮���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Πδ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һ�N�Ļ�ֵ˥��֮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п�ʹ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Ļ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@���˽���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Ե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݅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W(xu��)�ˣ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ӛ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�ʹ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Y��֮�űȣ��Р�֮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؞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Y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⮔(d��ng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ϼ�ʷ���cԊ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ɼ�̎��ϣ�D���ˁ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ʷ“������Ȼ֮��”��Ԋ“�t������Ȼ֮��”����“Ԋ���ձ���vʷ�tӛ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҇�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ֱ“����֮�H”����ͨ“�Ž�֮׃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“�ձ�”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“��Ȼ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ʷ�����^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֮�С��X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v“ʷ�N(y��n)Ԋ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Փʷ�ҿ���“�ҔM�O(sh��)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뮔(d��ng)Ȼ��”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(x��)�N���“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Ժ��”����Մˇ䛡����\��˹�ԣ�Ȼϧ���X��ֻ���ČW(xu��)֮�����c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̫ʷ��֮“˼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“Ԋ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и�һ�g�����֮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ڴ˴��Е�(hu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һϵ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ʮ��֮�ã��^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S��ľ����֮���}���|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֮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(sh��)��һ��ϵȫ��֮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ʷ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ڴ��c(di��n)ע�⼰֮Ҳ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˼��”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r(sh��)�f“�����@һ��֮���ѳɞ���H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ϵ�y(t��ng)�е�һ�h(hu��n)”���ʲ����^��ϵ“ȫ��֮�p��”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ʮ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҂���(x��)��ʡ˼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Ԯ�(d��ng)���Ļ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(zh��n)�Ը�ָ��V��Փ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編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|�о�ԺԺ�L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leon vandermeersc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Ļ�Ȧ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“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ȵ�ͬ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˾ͽM�ɞ�һ��(g��)5000�f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Ⱥ�w���H���B���Ї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x�c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Ј�(ch��ng)�ļ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֏�(f��)�h�Ļ�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Ļ�Ȧ������Ӱ푱��^(q��)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”�˷�Ԓ������һע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҂����ò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Ƕ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
�����棡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֮��׃���棬�L��֮���δ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砀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|��”����ָ�n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֮��δ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45��Ԋ�ƣ�“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”��“����һ���ξ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1948��Ԋ�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Ԣ���P(gu��n)�K���J�D�|�����[�n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n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K���γɣ��n��(zh��n)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Z���ް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u�����η��Ѿ����ǝh�Ļ�Ȧ���w���(y��n)�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֮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֮�ք�(sh��)��U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Ļ�ʷ�^�c(di��n)“����ʢ˥�B�h(hu��n)”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һ“δ�K”֮��֡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O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ʷ�P��Ȼһ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ĸп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Ї�δ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cԽҊ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֮ƪʲ�ښ��I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Ҋ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־�����°�֮۫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Ԯ�(d��ng)��֮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(y��ng)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媚(d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r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T֮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ɪ֮С�D���֞鮔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߳��@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δ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f�ɺ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ʹʷ�¼��f”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ʷ”�c“Ԋ”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档“ʷ”���dȤ�����һ؞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d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н�Qһ�ΑҰ�����ϴ��һ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ÿ��¶��Ī����죺“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“……���팍(sh��)�£��K�����Ҝ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ȵȡ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ڱ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“���Ƹ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o��”�ĺ�?x��n)|��ҕ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(li��n)�뵽�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ČW(xu��)�ڮ�(d��ng)���Ї���“���g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_”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t�҂���Ɇ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֮�g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^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(f��)�Ў����գ�”��“Ԋ”�Č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һ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Ů�B(t��i)ȫ��”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˥�̳��Ů”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ƫƫ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Ψʣힼt�y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Ŀ��ļ��H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֮�H��һ�N���е��f����“��ʮ�f�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Ѓ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Ѓ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Ů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Z�xϵ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Ů��”֮ؑ��(ji��)��ʿ��֮�⹝(ji��)֮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˚⹝(ji��)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y(t��ng)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ӵ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50�꿯�У�1955����1959����ӆ��ӡ�ġ�Ԫ��Ԋ�{�C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(hu��)�L(f��ng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y׃��֮�r(sh��)��ʿ����A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Ф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���䲻���m��(y��ng)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c��(x��)��֮׃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һ؞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˸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Ԋ��C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DŽ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x��n)|��֮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S���E֮���P(gu��n)�߸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Z��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y��)�в��ܲ��f����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ӵ�ijЩ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˱�ժ�����`��֮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Ԋ�˚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Ѓɗl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“�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֮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Ɛ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Ҋ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p3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¡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ӛ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rȪ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V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裨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ʯ�����R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㡌�(du��)�X���ԣ�“��˼��o֮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ˌ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ʹ��һ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@�l���ϘO�Ɍ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ɴ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“�xʷ�f֪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“��׃?c��)�֪ԭ���?rdquo;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Ժ���Ԋ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Ʃ���f����ͯ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A(y��)�е���͢�ĸ����c���µĴ�y��“���w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㡼Ҿ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ż�z���ϣ�……��(d��ng)�x�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зQ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㡪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n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ݷ��v�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_”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01��ꐼҶ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1902����㡼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һ�A(y��)�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H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˷f���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¿���“ǰ֪”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Z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c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@�Ԟ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Z�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Ħ���֮�Z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г��к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һ���鮔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“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ڴT�������տ˼��ͨ�R(sh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C(j��)�|��(hu��)��̽���[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տ˼��ͨ�R(sh��)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ڴ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“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һ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Ԋ�o(j��)�¡���ʮ���(c��)���⳯�����@Ԋ���P(gu��n)עጣ��֣�1966�꡶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ƣ�“һ���S�ݠ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h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傀(g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y��)�Ծ��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v��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ĸ�”ǰϦ��196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˼��“��C(j��)�|��(hu��)”֮�H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ɿ��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x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ټ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Փ�ģ�һ��һ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x�䡶Փ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ʷ�۹�
������Փ�n�����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ߣ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һ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ɰ�ʷ֮�y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(j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Ǵ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С���(zh��n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س�֮��ʿ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Пo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t��֮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x֮����y�A֮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֮˼��Ҳ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Փ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ķ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ĵ����w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ʷ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ʷ�ϵķ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İ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С�����A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e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Փ��ֻ�ķ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ȥ�϶�“�����d��”�f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ϲſ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֮“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Ļ��ϵ�“�����ŷ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Ļ�֮�����Ь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P(gu��n)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ʷ�y������ƴ�֮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h�ˡ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d��”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¶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ˡ�Փ�n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һ�N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ʷ���ČW(xu��)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۹ⲻ��̫�̜\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Ļ�ʷ�۹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ߌ��n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ʷ�Ϝ�(zh��n)�_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ǰ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f���µ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c(di��n)֮���ǰ�ڽY(ji��)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֮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w���Խ�֮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˼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Ҋ�^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n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҂��ƺ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ώ��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϶���“�ŷ�”�ķe�O���x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t�oһ�����ָ؟(z��)�n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“Ψ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⽨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Ă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Ҋ�T���@�N���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η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q�C”˼�S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һֱ���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̓�ٵ�“�q�C��”�����X��ǡ�����Փ�n�����t�҂�Ҋ�R(sh��)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C˼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@ʾ��һ�N�q�C˼�S�ľ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“�෴���m���”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һ�N�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f��“�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ŷ���@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֮������M֮����δϤ������횼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f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(sh��)�Ԕ��f�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Z�ɲ�Ԕ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U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(ji��ng)Ҵ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Ԕ��f���ɼ��f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ƪՓ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ŷ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@�Ļ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n��˼��ķ��W(xu��)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ǧ��δ�l(f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A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\(y��n)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¼{������֮�x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C˼�S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һ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ȫ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ǽ���ڲ���֮�űȡ���?zh��n)�֮��ӆ�ĵ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��c�K�O�P(gu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ɼ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ͬ�꣨1951������Ԋ�䣺“ͬ�ò�Ϫ�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f�xѩӯ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(ji��n)��“���|�f�x”��“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^�ѷ�ǰ�Ș䣬�֪q����ߘ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O(ji��n)�ն�ʿ���ϸ��|��ʣ��(d��)�n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ڮ��|(zh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�Ї�˼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“�˹�����ԇ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г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Ů����Ц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”�Լ�“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w�f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һ齻���λ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ꎳ�Ļ �Q�s������”“�s�Q”���O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ڌ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@���H�nj�����Փ�n����һ�ĵ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؞���Ļ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“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ݔ�����֮�W(xu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λ���˶��N�෴���m���֮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澫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f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|ʷ֮����ʾ��Ҳ”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m�Ї��܌W(xu��)ʷ�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K�O�P(gu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K�Dz��ɷ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Z��
�����̴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մ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��ߡ�……
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ϡ�Ԋ�ƣ�
�����O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´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d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ѹ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Ą�(d��ng)�C(j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Ӣ�r(sh��)�f��“���X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fȥ���}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˪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“һ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²����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Ξ�ѱ�”���}���Ԋ�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f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˪�tһ���ќ�ɣ��”“��”��“�d��”��ŵ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ͬ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11688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���ŵ伴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һ�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r(sh��)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Լ����£�
������㡰�������֮ȡ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(d��ng)�Տ�(f��)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T�z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h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n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���S�Ԟ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t���o�֏�(f��)��ԭ֮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ƾӳǃ�(n��i)�fլҲ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?x��n)|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ǰʼ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�(f��)�d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ͨ�q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֮���S֮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Ѕ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֮�Ը�ͬ���˼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QҊ�ӡ�
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o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v��“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֮��ͬ”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X�¡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ӛꐷ��˸�����ʧ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51�� �f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֮�I(y��)�f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Ԋ�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(d��ng)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Ԫ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ǧ�ﺲī�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塷�L��“����h�Q�U������Λrǧ�ﺲī��”֮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~���֪�
��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ٌW(xu��)�n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һ��֮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֮�匚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o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^�c(di��n)��(du��)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ߵĶYٝ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ʷ��־���C��
�����Ї��Ļ�“�v��(sh��)ǧ��֮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w��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֮�l(f��)չ���ض���“�ΌW(xu��)֮��(f��)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댦(du��)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ٷ��Ϻε�������˥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���1964)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ۙ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첻�ɼ����ͽ��֮��(m��ng)�¡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㡵Ă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ġ�ʷ�����㡂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|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㡵�����ʮ�꡷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K�x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]�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Փ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“�Ļ�����”��ϴ�Y�c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66��7�£��ڴ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ֈ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qՓ��“�Ĵ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У�@��(n��i)�u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R˻�����ֈ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Ĵ���̖(h��o)“���Y��”��“�Y�a(ch��n)�A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(qu��n)��”�����Ҳˮ�q���ߵر��ӷ��“ţ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“�⽨����”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Ļڵ����Y��”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ؔ(c��i)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(j��)�o(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ۇ����x��ˎ�ﲻ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Ů�o(h��)ʿ�ȵ�“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?rdquo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ԭ���ϵ�һ��ӛ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ĸ�”���F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ѵ����㡸���ѩ�ϼ�˪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汻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Tֱ���P(gu��n)�Ѷ�ί�ɵ�ꐼҵ������o(h��)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㡹��Yͣ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ꐼҾ�ס��У�@��(n��i)�|�υ^(q��)һ̖(h��o)�DZ����ֈ�(b��o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h(yu��n)��ȥ��ͬһ�ھ�İ�ɫ�ײ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ژ�ľ������У�@һ�磬��֮���˿ֲ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ֈ�(b��o)�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T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㡵��·��Ͻ��ɴ��ֈ�(b��o)�N�w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o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“��߀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”�İ�Թ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췴�ɂ�Ҋꐼ��m��“�_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߀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г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ؔ(c��i)��Ĵ�Ҏ(gu��)ģ�Є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㡺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ĕ���ȫ����⣬�ָ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o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㡚v�Mǧ�y�f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Mʮ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e�ұ������Ķ�ʮ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״�“��(zh��n)��ϴ�Y”�������ꐼ�ؔ(c��i)��Mʧ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K�O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ю�ֻ���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լ��ǰ�ݺ��� ȡ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ŭ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Ŀ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R�һ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ʧ�߰Y�c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ׂ�(g��)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ڶ�߅в�ֹ����@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̻̲��ɽK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Ҋ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Ӵ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ɴ���M(j��n)�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^֮�ϡ�ÿ��(d��ng)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լ����j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D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p�p���K����(f��)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°�ĭ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69�괺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ұ��ߵس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д�У�@���υ^(q��)��ʮ̖(h��o)һ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㡲��w˥�����Ѳ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M(j��n)һ�c(di��n)��ˮ֮�“��ʳ”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H��͵͵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۽Dz����М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ߟo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״α����T�� 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yȭ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څ��(y��n)�؎��c�����ƹ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SȪ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Ϣ�����㡑z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\(y��n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đџo�M��Թ���c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衶��Ԭ���: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ţ�£��c�d�����c��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y���[����Ȫ�Դ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69��5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Ϛ��}�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α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ҬF(xi��n)��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֮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I�M��Ѫ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�7�ճ�5�r(sh��)30�֣�����˥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º��11��2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o������徣��S���㡶�ȥ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һ�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ס����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᷷��˸����K�ڻؑ�䛡���᷺��ҡ����f:“�Ǖ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Ҍٶ��e���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͑�(zh��n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t�l(w��i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֪ͨ�_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һ��Ҳ����С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vʷϵһ��(j��)�̎������pĿ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đ��С���һ Ҋ�����ﺰ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͜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ӣ��K�ڽo��?bi��o)��ˡ?rdquo;
����̩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һҊ��ʷ�W(xu��)�ʹ��h(yu��n)ȥ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1964�꣬�����ڡ�ٛ(z��ng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“���v��(sh��)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L��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ɸ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ۙǰ�t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z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첻�ɼ����ͽ��֮��(m��ng)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ٕr(sh��)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f:“�mȻ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ٌW(xu��)�n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죬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һ��֮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֮�匚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o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ƪ��Ѫ�ΜI֮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Ļ�ѳ���ߵ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Ҳ��һλ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[�Z��
|
| 1062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ٰ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423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ʮһ |
| 1704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_˹Ů?d��ng)z�����Ɓ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x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722��7��3���峯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ʩ���]���� |
| 1844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l�s����ӆ |
| 1883��7��3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m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889��7��3���Ї���?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֮���� |
| 1890��7��3���Ї��v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㡳������ |
| 1898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ó��� |
| 1898��7��3���ЙC(j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S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02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yϯ������ϲ� |
| 1904��7��3���ƌW(xu��)�a(b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04��7��3���q̫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I(l��ng)��մĠ����� |
| 1905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 |
| 1907��7��3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С�f��ʒ܊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14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ˈ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R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¿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14��7��3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ӆ����ķ���l�s�� |
| 1921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{(l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23��7��3��Ӣ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Ї� |
| 1924��7��3���V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v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ʽ�_�W(xu��) |
| 1924��7��3���¼��¿��y(t��ng)�{����� |
| 1928��7��3���ҕ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ռ� |
| 1929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a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 |
| 1929��7��3���й����K���ӹ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Hί�T��(hu��)��ʮ��ȫ��(hu��) |
| 1930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ָ�]�ҿ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31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 |
| 1934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ֱ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 |
| 1938��7��3���Ӱ���˰ى�ʿ���ڇ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40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A�M(j��n)�м�(x��)����(zh��n) |
| 1942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c�^�m(x��)Մ�� |
| 1942��7��3���й��M����·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x��)x���� |
| 1957��7��3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R�ֿƷ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з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 |
| 1962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檚(d��)�� |
| 1962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R�]��(d��ng)�tӰ�ǜ�ķ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68��7��3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ˇ�˅�ٻɏ������� |
| 1978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R�d�����l�s��ӆ |
| 1978��7��3���Ї�ֹͣ��(du��)ԽԮ�� |
| 1980��7��3���_���ό����A�c���L�o�����K��70�q |
| 1987��7��3��f1�tţһ�(du��)܇������˹�ٰ����S�ؠ����� |
| 1993��7��3�����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Ⱥ |